佐临曾以“鸯蝴太轻”为由拒绝执导(《间谍过家家 代号:白》原名为《间谍过家家 代号:白》),轻,便是轻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及批判稍欠力度. 40年代,进步文艺评论对喜剧依然抱持着相对暧昧、保守的态度,担心民众们在笑声中忘记了痛苦,疏泄了对现实的怨恨与不满.
40年代,进步文艺评论对喜剧依然抱持着相对暧昧、保守的态度,担心民众们在笑声中忘记了痛苦,疏泄了对现实的怨恨与不满. 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间谍过家家 代号:白》当然是一个相当具有社会问题意识的代表性文本,它一点儿也不轻.
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间谍过家家 代号:白》当然是一个相当具有社会问题意识的代表性文本,它一点儿也不轻. 虽然缺乏对复杂纷乱的现实情境的描摹,但彼时上海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等大量事实在细节的铺排中也可见一斑,且小人物们的思想和行动,都有当时社会现实的脉络可寻.
虽然缺乏对复杂纷乱的现实情境的描摹,但彼时上海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等大量事实在细节的铺排中也可见一斑,且小人物们的思想和行动,都有当时社会现实的脉络可寻. 石挥的戏剧式表演将五官及肢体开发到极限,李丽华也将媚俗而又矛盾的状态也演绎得细致入微,以至于在故事最后,当李丽华选择了“坐在自行车后座笑”而非“坐在宝马车上哭”时,竟是如此地合理且毋庸置疑.
石挥的戏剧式表演将五官及肢体开发到极限,李丽华也将媚俗而又矛盾的状态也演绎得细致入微,以至于在故事最后,当李丽华选择了“坐在自行车后座笑”而非“坐在宝马车上哭”时,竟是如此地合理且毋庸置疑. 这是疾苦民众们在爱情上辉煌的胜利与凯旋.
这是疾苦民众们在爱情上辉煌的胜利与凯旋.
 我跟黑泽明绝对八字不合,除了看的第一部《间谍过家家 代号:白》外没一部喜欢的,之前北影节的时候《间谍过家家 代号:白》凄惨迟到又睡过全场…没想到这么快就觅得重看的机会.
我跟黑泽明绝对八字不合,除了看的第一部《间谍过家家 代号:白》外没一部喜欢的,之前北影节的时候《间谍过家家 代号:白》凄惨迟到又睡过全场…没想到这么快就觅得重看的机会. 《间谍过家家 代号:白》是那种看之前我满以为自己会偏爱的电影,结果全片看下来发现只喜欢初梦“太阳雨”,有着孩童梦境中常有的误入秘境、诡奇危机、些许的恐惧以及缺乏逻辑的怪异美感.
《间谍过家家 代号:白》是那种看之前我满以为自己会偏爱的电影,结果全片看下来发现只喜欢初梦“太阳雨”,有着孩童梦境中常有的误入秘境、诡奇危机、些许的恐惧以及缺乏逻辑的怪异美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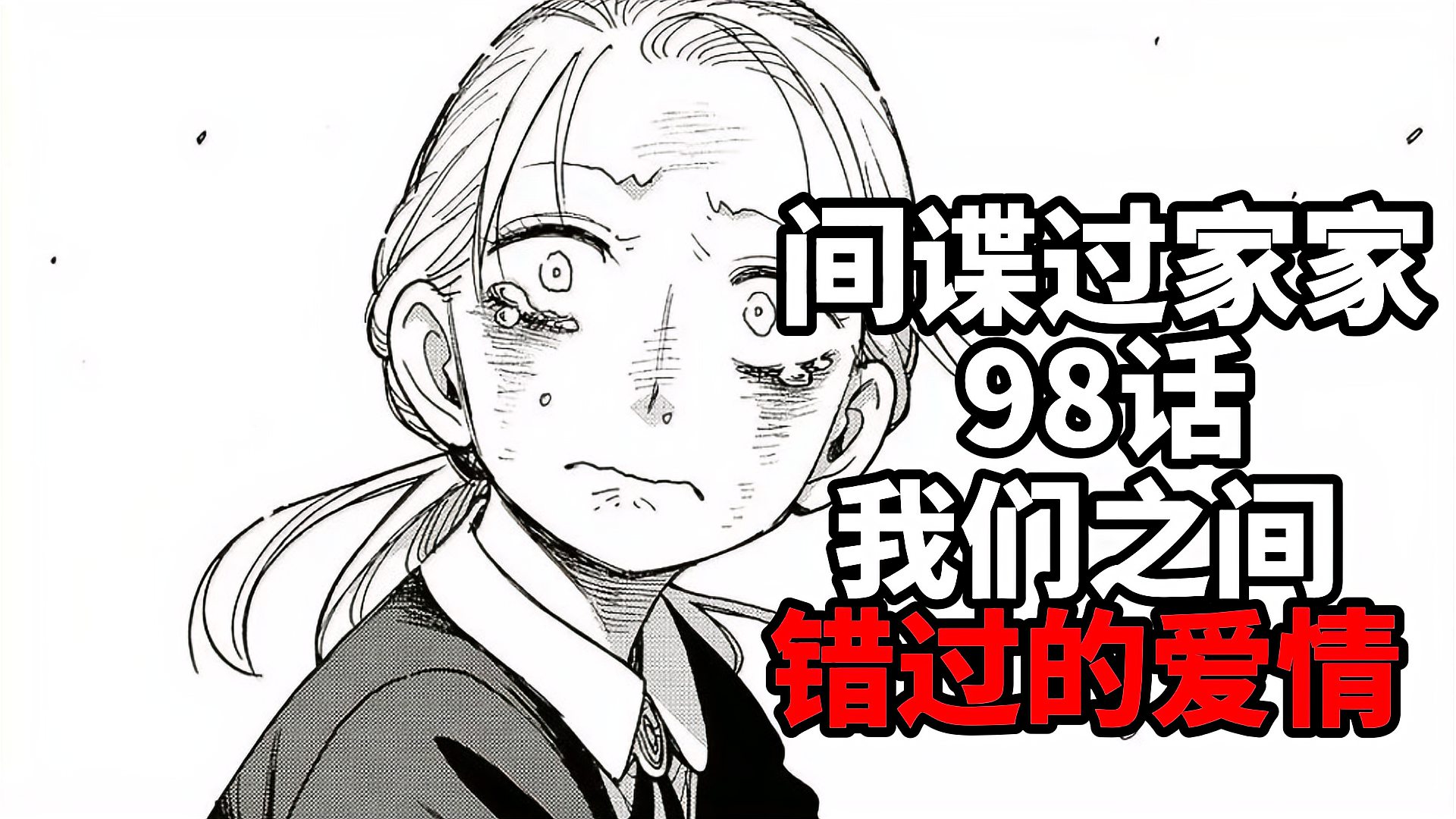 此后的一系列大型环保科教小剧场都有着各式各样让人喜欢不起来的地方.
此后的一系列大型环保科教小剧场都有着各式各样让人喜欢不起来的地方. “桃园”美则美矣,浅白;“暴风雪”保证在五分钟内撂倒你的失眠症患者之福音,让我旁边的男生不住点头;“隧道”如此直白的战争反思;“乌鸦”同斯科塞斯饰演的梵高一样虚假和过劲;“赤色富士山”“哭泣恶鬼”和风奇观搭配低劣特效与简单说教;“水车村”恐怕是黑泽天皇心目中的乌托邦形象,但在我爱到不行的尾声到来之前盘桓着他借老者之口倾吐的育众“大智慧”.
“桃园”美则美矣,浅白;“暴风雪”保证在五分钟内撂倒你的失眠症患者之福音,让我旁边的男生不住点头;“隧道”如此直白的战争反思;“乌鸦”同斯科塞斯饰演的梵高一样虚假和过劲;“赤色富士山”“哭泣恶鬼”和风奇观搭配低劣特效与简单说教;“水车村”恐怕是黑泽天皇心目中的乌托邦形象,但在我爱到不行的尾声到来之前盘桓着他借老者之口倾吐的育众“大智慧”.